原创 特朗普的关税出问题了:法院说他越权,欧盟白让步,美国自己乱了
今年7月18日,欧盟与美国刚刚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贸易协议。在这份协议中,欧盟方面主动作出让步,同意对出口至美国的商品额外征收15%的关税,试图通过这种单方面的妥协来避免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一个多月后的8月29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以7票赞成、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作出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政策存在越权行为。这一裁决使得欧盟此前作出的所有让步瞬间失去了实际意义。

裁决公布的当天,光明网就发布报道称,欧盟委员会正在紧急推进一项新的立法程序,计划取消对美国工业品征收的关税,同时要求美国在汽车关税方面给予相应优惠。这样的发展态势完全不像盟友之间的正常合作,反而更像是欧盟刚作出让步,美国就立即翻脸不认账的尴尬局面。特朗普政府当初是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作为法律依据,试图绕过国会审批程序直接对全球商品加征关税。但法官在裁决中明确指出,这种做法就像用锤子来拧螺丝,完全用错了工具。这部法律原本是为了应对特殊紧急情况而制定的临时措施,绝非用于改变全球贸易格局的常规手段。

司法系统此次出手阻拦并非针对特朗普个人,而是为行政权力划定明确边界。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一直在收紧行政部门的权力范围。2024年最高法院驳回拜登政府学生贷款减免计划的判决,就是基于重大问题原则,即行政部门在推行重大政策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无疑是个不利信号。面对裁决,特朗普态度强硬地表示将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根据央视新闻8月31日的报道,最高法院可能要等到2026年才会审理此案,整个流程预计需要两年时间。考虑到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大法官占据6席的优势地位,最终结果仍充满变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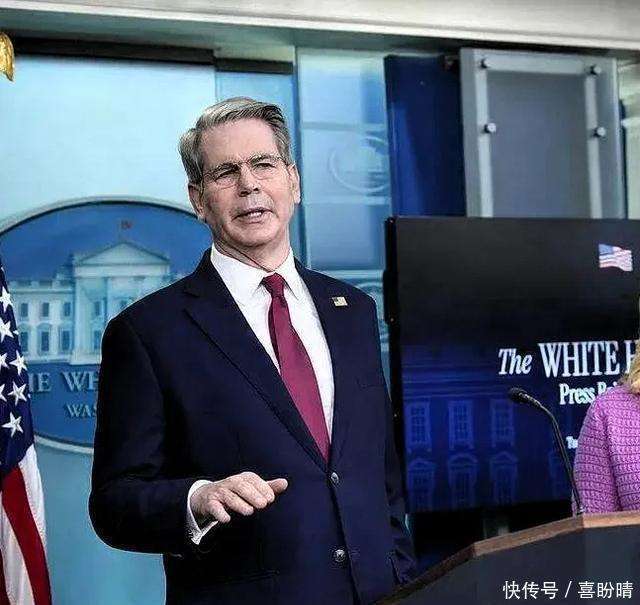
美国商界对此反应强烈。汽车制造、电子产业等依赖进口原材料的企业陷入两难困境:调整供应链可能面临政策反复的风险,不调整又担心关税取消后成本压力骤增。美国商会在8月28日发表声明,敦促国会尽快通过立法明确关税权限。政策的不确定性让企业连半年后的生产计划都难以制定。这种局面非但不能保护本国经济,反而让国内市场陷入混乱。特朗普坚称加征关税是为了迫使盟友让步、保护美国利益。但光明网8月13日的报道显示,美国制造业所需中间产品有半数依赖进口,早已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
如果按照裁决取消关税,中小企业将面临成本激增的困境;若维持现状,中国网9月2日的报道指出美国可能损失159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相当于联邦年度教育预算的37%,这对本就紧张的财政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美国内部的分歧加剧了全球避险情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28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3.3%下调至2.8%,并明确指出美国关税政策是主要风险因素之一。面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各国纷纷寻求替代方案:日本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的自贸协定,欧盟调整对美关税政策,拉美国家加强区域合作。
有人将特朗普的政策与2002年小布什的钢铁关税相提并论,但两者有本质区别。小布什当年对27种钢铁产品加征8?0%关税后被WTO裁定违规,而特朗普此次涉及1200多种商品,范围扩大44倍。更重要的是,小布什是政策制定存在疏漏,特朗普则是试图突破制度约束,让行政权力凌驾于国会和法院之上。结果不仅未能保护经济,反而引发对美国政府权力边界的质疑,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
特朗普政府面临两难选择:上诉寄希望于保守派大法官的支持,或接受裁决调整美国优先政策。无论选择哪条路,美国都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行政权力越界与全球化趋势背道而驰,内部纷争和对外施压只会让局面更加复杂。这场争议的核心在于美国三权分立体系的失衡。特朗普试图用应急法律改变贸易规则遭到司法阻挠,反映出更深层的制度危机。比1590亿美元损失更严重的是,美国将权力之争演变成内耗,同时无视国际规则。这不仅可能使特朗普的政策陷入僵局,更可能削弱美国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这场风波犹如一面镜子,照出美国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困境:高喊美国优先却连自身权力边界都未厘清,期待盟友配合却无法保证政策稳定性。无论最高法院如何裁决,美国都需要认清一个事实: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单边主义和内部纷争只会逐渐丧失竞争力。如果特朗普政府不能吸取这一教训,美国未来还将面临更多类似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