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再次挥舞关税大棒,这次识趣的特朗普,对中国换了个打法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问题最近成为了许多国家关注的焦点,几乎成了头等大事。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关税政策的变动让各国政府不得不对其未来的贸易战略做出深思熟虑的调整。

截至7月7日,特朗普签署了行政令,延长了“暂缓期”,但是,除了英国和越南,其他国家依然未能和美国达成关税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关税名单中并未涉及中国,这让特朗普不得不改变策略,选择了另一种“手段”。

作为美国第二任期的总统,特朗普的“朝令夕改”已不再是新鲜事,反而成了一种常态。比如,7月2日,特朗普才刚宣布美国与越南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约定越南对美零关税,美国则对越南商品征收20%的关税,同时对通过越南转运的第三国商品加征40%的税率。表面看似越南的妥协,但实际上却间接伤害了中国的利益。越南经济相对较小,之所以能在2018年至2024年间,其对美出口额从不足500亿美元增长至1370亿美元,关键因素在于中企投资和转口贸易。
次日,中国外交部即作出了回应,坚决反对任何通过牺牲中方利益的方式达成交易。显然,特朗普对越南在关税谈判中的妥协表示满意。在7月4日的讲话中,他透露,美国可能会单方面向多个贸易伙伴发函,规定具体的关税税率。记者询问他如何处理超过100个国家时,特朗普回答道:“每天发10封。”他还表示,不会推迟原定的截止日期。

不过,几天后,特朗普可能意识到发函的进度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于是他选择通过签署行政令,延长“对等关税”暂缓期,从7月9日推迟至8月1日。由此,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1.0”阶段结束,进入了“2.0时代”。

不少人会疑惑,既然特朗普与日本和韩国的谈判不太顺利,为什么不直接加征关税,而非选择延迟呢?根据彭博社和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特朗普的这一决定是为了拖延时间,避免在年底圣诞节的消费旺季,美国市场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
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特朗普本身的政策立场和美国内部的矛盾。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背后扶持的经济利益也大为不同。民主党一方面口号高喊“保护环境”,背后是新能源企业提供的竞选资金,而特朗普则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帜,推崇制造业回流,并大力支持传统能源。“大而美”法案的核心,正是扶持传统能源产业,而马斯克等新能源企业则常被特朗普批评为“夕阳产业”。

这时,日本和韩国的汽车产业便成了关键因素。如果日韩也像越南那样向美国妥协,特朗普就能宣称他为美国汽车行业争取了更多利益,比如便利的出口政策,同时不会影响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事实上,特朗普再度挥舞“关税大棒”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无论日韩如何应对,美国最大的外贸竞争对手始终是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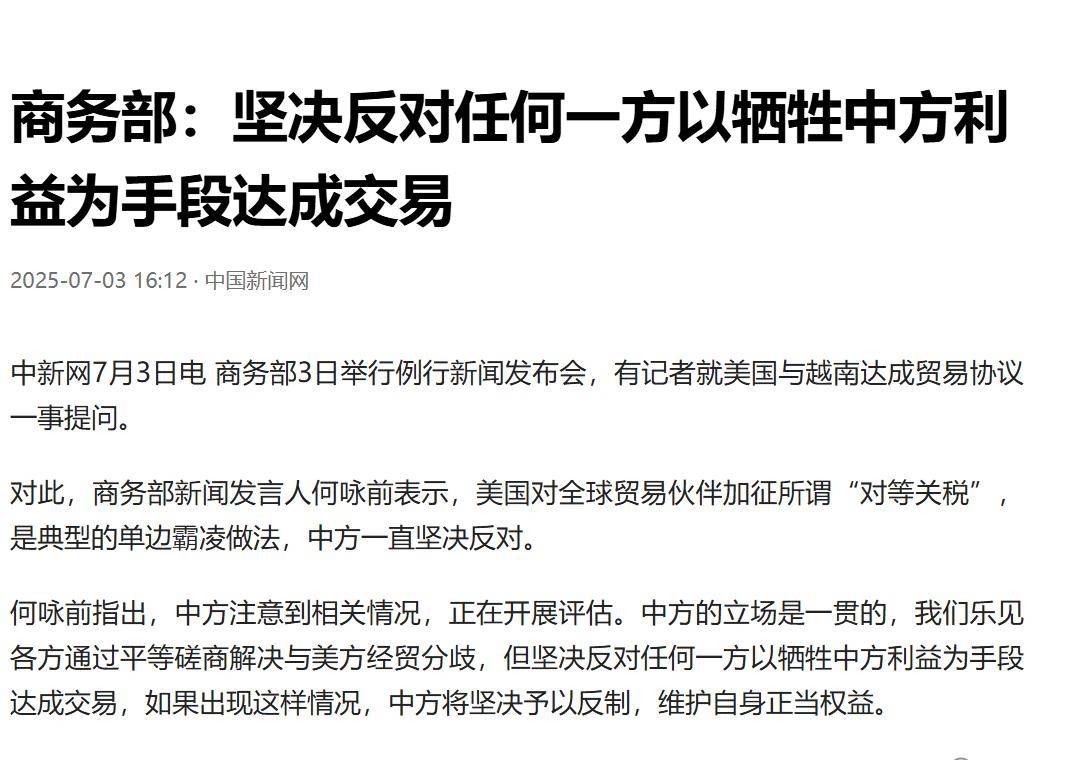
尽管如此,中国和美国在5月进行的关税谈判中的“暂缓期”却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暂缓期”将持续到8月初。经历了两轮谈判后,特朗普逐渐意识到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他开始调整对中国的策略,改变了原有的关税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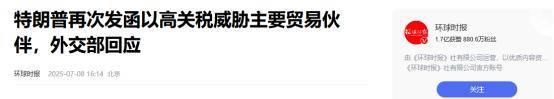
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正面临两重矛盾。首先是“鹰派”和“温和派”对加税政策的不同看法。例如,在日本谈判破裂时,美国代表卢特尼克与贝森特现场发生了争执,让日方代表感到措手不及。其次是美国的“盟友”对关税的态度。像英国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和美国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利益冲突。英国早早和美国达成协议,韩国则因政治因素推迟了谈判。
因此,特朗普选择延长“暂缓期”是有其战略考虑的。直接从中国手中拿到稀土显然不现实,而越南的“妥协”给了特朗普新的灵感。他试图通过施压中国周边国家,迫使它们签署类似越南那样的不平等协议,从而间接损害中国的利益。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策略得到了“大而美”法案的支持,这为他提供了更多的筹码。美国每任总统都会推出一项标志性的法案,奥巴马有“医疗改革”,拜登有“通胀削减”。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虽然看似有些“拆东墙补西墙”的意味,但实际上是为了加强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对日本汽车产业提供了政策支持。

至于韩国,虽然李在明总统走的是“务实路线”,在中美之间尽量保持中立,但如果特朗普的条件足够吸引,也不排除“务实”的韩国再次倒向美国。
总结来看,特朗普在宣布“延迟”后再度宣布“延期”,本质上还是基于“美国至上”的原则。无论是拉拢韩国这样与美国利益相近的国家,还是通过施压其他国家,迫使它们通过牺牲中国利益来达成协议,特朗普的最终目标无疑是制约中国的崛起。面对这一局面,中方已表明,若再出现像越南那样的情况,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距离8月1日的最后期限尚有一段时间,如果到时特朗普的“盟友”们还未与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会再次“延期”吗?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关注。

